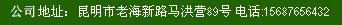|
7)火车顺利抵达郑州站。听播音员在喇叭里说,火车将在这里停留几分钟之后才走。郑州是个大站,我以为会有很多旅客在此下车。有空位的机会来了。哪晓得是上车的人多,下车的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记。伺机抢个座位的希望一时间化为泡影。 “检票了,检票了。”随着检票员的一声叫喊,车厢内顿时噪杂声四起。空气里也弥漫着各种气体,很是难闻。 “你,车票?”检到我了。我将车票递过去。那检票员瞄了一眼车票之后,再将车票翻了过来,皱着眉头看了好一阵子。 “难道有什么不对吗?”我有些不明白。别人的车票他看一眼就退了回去,为什么我的车票他要一看再看?看这么仔细干嘛呢? “身份证拿出来。”检票员有些异样。当我递过去身份证后,检票员要我跟他去一趟。我这时才感觉到,有可能在宜昌火车站被那年轻人骗了。 果不其然,当我被带到值班室时,一名乘警告诉我说:“你的票是假的,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。”我恍然大悟。可惜后悔已晚矣。紧接着,是那乘警安排我在值班室里说情况,录口供,按指印,搞得一塌糊涂。虽最终认定我不是嫌疑犯,也没让我为此事件负责,但去补票窗口补票的命运还是降临了。 几经周折,我于十三日深夜抵达北京火车站。刚走出站口,一股透骨的寒气陡然袭来,身体的每一块肌肉、每一根神经都在不停地哆嗦。原来我铁打的身子骨,到了北方怎么会如此的不堪一击?脆弱到走路也颤颤巍巍?还好,军用包里有师娘送的皮衣。穿在身上果然凑效。 之后,我想放眼一下远方再走,却被不知名的高楼阻挡。那就改变一下视线,昂首一下苍天吧!哪知道苍天惊人的狭小,几乎可以用一根黑黢黢的布带子来形容它的窄。那故乡皎洁的明月,没看见,那故乡满天的繁星,也没看见。只有车流如萤火。顺着城市的血管极其规则地蠕动。今夜赶去文联出版社是完全不可能了。只有先找个旅馆住上一宿再作打算。 我所在的站前广场就有好多推销住宿的说客,甚至打出了“包接包送”的广告牌。经打听,价格都比较贵,一般都在六十至八十元不等。那可是我半月的工资啊!这样的旅馆,我有些消费不起。再者,这路边的推销,说不准又会诱惑我上当,还不如亲自去附近找找看。我扛着军用包,在周边巷子里转悠了一个多小时,其结果更令我失望。大多都在百元以上。咋个办呢?还是回头找那推销的旅馆吧。一些事物,往往真的会事与愿违。当我再次回到站前,哪里还有推销旅馆的说客呢,只有脚步匆匆的旅客和偶尔“嘀嘀”的出租车从我身边流走。 迫于无赖,我来到灯火通明的售票大厅,条椅作床,行囊作枕,手拿一本诗书熬到天明。 8)十四日中午,我来到了一个叫“豆各庄”的地方。那里有一个叫“承德大楼”的宾馆,是《通知》报到的地方,也是我梦中的仙境。报好到,登好记,交好稿,看好房,洗个澡,然后蒙头补觉。想以最佳的精神状态迎接十五日的会议开幕式。 没想到的是,就在傍晚时分,我出去吃晚饭路过宾馆大堂,和服务员闲聊时得知,这次来开会的学员总共才登记了五个人,这其中还包括我。 怎么会是这样呢?我问服务员:“你可知道,他们总共通知了多少人?” “好像是两百多吧!”那服务员不敢确定具体是多少人。 这就奇怪了,全国那么大,通知了那么多人,难道就我们五个人是真心的酷爱文学?难道我们这五个人是患了文学梦想综合症?是傻子?是疯子?难道我又是被骗了?我很是伤感。但转念一想,被骗应该是不会。因为就在宾馆的外墙之上,还悬挂有《人民文学》培训中心的牌子呢。人民文学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刊物,在它眼皮子底下做小偷小摸、骗文学小青年的勾当,这应该不合常理。怎样才能证明我们没有受骗呢?看明天会不会有《日程表》上所标注的作家们露脸不就明白了吗。我正在纳闷,住我隔壁的文友李葆华(是位女士)凑了过来。她来自包头,也是来参加会议的。她告诉我说,负责本次会议的梁晓明老师刚才已经来过了。 我忙问她:“梁老师怎么说?” “他说,这次笔会估计是因自费的缘故,所以远没达到预期的效果。”李葆华叹了一口气,“如果早知道是这样,我就不来了。遗憾啊!” 确实,这样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文学活动,竟然只来了五个人!如此糟糕的结果,不仅让文联的领导和作家们大跌眼镜,也令我遗憾万分。我千辛万苦筹钱,又千里迢迢来北京交诗友,寻名师,如今却落得个无友可交的下场。估计寻名师指教也会大打折扣了。哪有不痛心的呢!晚饭也不想吃了,便掉头回到了房间,准备继续蒙头大睡。 孰料,想沉沉睡下却偏偏难以入眠。在床上翻来覆去的,折腾了整整一宿。 天亮了,我早早的就起了床。北京的冬天,天亮得特别的早,大概四点多吧。我来到卫生间准备洗漱,哪晓得其余四个文友比我还要早,他们已经快洗漱完毕。我故意打探下他们的心情:“大家昨夜睡得可好?”他们一起苦笑道:“哪里睡得着哟!”看他们如我血色的眼睛,估计心情也不咋地,应该和我差不多,也糟糕透了吧。随后,我们便一起出去吃早点,闲逛,闲聊。一直等到差不多八点的时候,梁老师来了。他要我们去会议室“出席开幕式”。只有这么几个人,还出席个什么“开幕式”呢?我们虽然都有些惊讶和疑惑,但都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,去了。 9)好大一个会议室哟,简直就是一个大礼堂。在我的印象中,只有秭归大礼堂才有这么气派。那悬挂在主席台上的暗红色幕布,至少也有五六十个平方。几张用朱红色桌布包裹着的演讲桌,在主席台前一字摆开。上面整齐的摆放着七八个分别写有姓名的卡片,还有一台用红布包着麦克风的老式会议话筒置于正中。在灯光的照射下,显得格外的耀眼与庄重。主席台下,一堆杂乱无章的人姿势各异,或闲聊,或抱着写有这次会议主题的横幅指手画脚。估计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,或者是文联出版社的领导、作家们。可惜他们并没有去对号入座的意思。那与会区空无一人,座位倒有好几百个。只有我们五个人在梁老师的带领下,来到了最前排落座,才填补了与会区的空白。 “大家请注意”一个抱着文件夹的中年男人开始主持开会了,“由于参会的人数过少,经组委会研究,将开幕式改为座谈会......这样也有利于学员们能更好的和作家们近距离交流。大家说好不好?”也好,人少有人少的好处。假如参会人数上百,说不准和作家们说上几句话的机会也没有呢。经过这位发话的领导一提醒,我真的就改变了思想,失落感也瞬间消失。可我们中间,有一位年龄较小的文友,随即站起身来,说“我们是受骗了吧?我强烈要求:退钱走人。”看样子非常气愤,似乎并不理解组委会的难处。也不听主持人解释。梁老师立马走了过来,示意我们劝他先坐下。但他执意要理论再三。会议还在继续,主持人招呼我们和文联出版社的领导及作家们站成一排,将印有“中国文联出版社首届文学新人座谈会”的横幅展开,让摄像师为我们合影留念。那文友不愿近前,而是自己离开了会场。如此一来,我们的文友队伍再次减少,只有四位了。“开幕式”也就这样草草的收了场。后来听服务员说,组委会还是将会务费退给了他。 开幕式后,原定于由《当代》常务副主编胡德培主讲的小说写作培训,变成了在宾馆房间里的小说写作闲聊。下午和第二天,依然如此,只是作家变了。他们分别是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崔道怡,社科院文研所评论家曾镇南,北京出版社编审廖宗宣等。我交的是诗稿,也只喜欢诗歌,对于他们闲聊的小说和文学理论,我一点兴趣也没有,总是浑浑噩噩的呆在那里,像是在听外国人讲故事。其实,什么也没听懂。 我在等待中迎来了十七日的曙光。未完待续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作者谭家臣,男,曾用笔名“晓城”,七十年代生,湖北秭归人。自幼受屈原诞生地——乐平里诗歌文化氛围的熏陶,90年代开始习诗,亦习小说及散文。有作品两百余篇(首)散见《中国诗歌》、《诗歌文艺》、《诗中国》、《西部文学》、《黄河文学》、《齐鲁诗歌》、《北方文学》、《北方诗刊》、《中国青年诗选》、《三峡晚报》、《荆州晚报》、《三峡日报》、《宜昌作家》等纸媒;有多篇诗歌作品入选各种文学选本;有五十余万字的散文或小说散见《江山文学》、《中国作家网》、《中国诗歌流派论坛》、《凤凰网论坛》、《宜昌作家网》等文学网站。央视新闻频道、湖北新闻频道、湖南卫视、湖北广播电台、《湖北日报》、《三峡晚报》、《三峡商报》等媒体曾先后对其写诗经历做过专访或制作过专题片。现在某企业内刊供职。业余在晓城文字工作室兼职,任主笔。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,哈尔滨治疗白癜风的医院白癜风用什么药最好
|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新闻早餐201677星期四农历六月
- 下一篇文章: 行业资讯湘鄂赣省际交界区域强化联动治